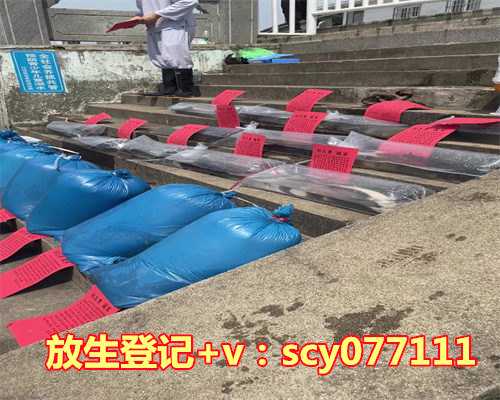学佛十年,出家为僧
---- 似乎每件事都有一定的意义,但究竟意义何在呢?目前我还不太清楚。它应该是人生蓝图的一部分,是人生固有的;也许直到死亡的那一刻,我才能领悟到全部的意义。尽管它牵引着我的每一步...
今年农历 7 月 30 日,----,我终于在地藏菩萨圣诞日剃度出家!这在全家人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。他们不仅惊讶,而且不解。条条大路通罗马,我为什么要选择它呢?在我的亲戚中,大姑的儿子现在是县委书记,二姑、三姑的儿女现在是大学系主任,而我父亲的儿子已经剃了光头,披上袈裟,做了和尚。当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时,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,等着我出人头地。现在我选择了出家这条路,难怪父母特别伤心,亲戚们也都很失落!
这几年我一直在学佛,没有任何宗教家庭背景的我,能一步步走上这条路,只能归功于冥冥之中指引我人生脚步的蓝图!
我生长在农村社会,父母信奉的是一般的祖传宗教,或者说是民间信仰!我不能说我不信佛,但我只拜佛。小时候,我对佛教的第一印象就是为死者念经、忏悔的仪式,闽南人称之为 "做功德",在当时除了 "吵死人 "之外没有任何意义。也许正是这种印象,让我至今都没有接受佛教的诵经、念经和忏悔。其次,在我小时候,旅游并不流行,尤其是在农村。如果不想走亲戚,就只能去寺庙拜拜。那时候,父母经常带我去寺庙,刚开始觉得挺有意思,但长大一点后,觉得去寺庙就是烧香磕头,一点都不好玩,就不去了。
上小学的时候,崇尚科学、破除迷信是很时髦的事情,尤其是大家都在讲国父小时候为了破除迷信,把神像的胳膊掰断的故事,让我们很是 "手痒 "了一阵子。有一天,我们竟跑到一座小庙里,用同样的方法戏弄了它一番,才大呼过瘾。总之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对佛像、僧人,是没有一点好印象的,虽不至于 "快意恩仇",至少也是不屑和关注吧!
而在农村长大的我,思想单纯,就像动物一样一天天长大,从来没想过 "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 "之类的问题。我从来没有想过 "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 "之类的问题。我既没有感受到世间的幸福,也没有感受到众生的苦难,在我的人生境遇中,我似乎与这些问题无关。佛法与我就像两条平行线,各行其道,永不相交。
在我上高中的时候,化学课上讲到,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,原子一旦分散,万物就会发生变化。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物质生命,生而不生,灭而不灭。第一次重温生命的自我,是在电视剧《功夫电影》的时候,里面老和尚对小蚂蚱的开示,既玄妙又精妙,如深山古乐,发人深省;当时我并不理解,但一直为之着迷。生命的蓝图蛰伏了十几年,却在慢慢苏醒!在未知的远方,似乎有一个磁场,正牵引着我的脚步,我情不自禁,心也不知不觉地迎合着它。
后来,我读了一本书,《厚黑学》;书中作者将世界上所有的哲学都按其深浅确切地列出了等级,并对一位厚黑学大师的教诲赞不绝口,佛心显然不是盖的,于是佛心在我心中便有了地位。
长大后,我开始思考生命和世界的本质。当时,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迫使我去研究和处理它们。但是,在我的内心深处,一直渴望对世界的方方面面有更深刻、更清晰的认识,希望它能够一以贯之地成为一个完整而庄严的体系。因此,我阅读了大量当时流行的 "新潮文库"。慢慢地,我得出一个结论: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不在于他所处的物质环境,而在于他的思想和性格。如何树立正确的心态,培养开朗的性格,需要深刻而明晰的哲学指导。我确信,这种哲学就是佛教。尤其是当时,我刚刚读过老庄哲学。虽然老庄哲学一直被认为是消极无为的哲学,但我从它 "反常道而行之 "的方式中看到了它更积极、更有意义的一面,佛教不也是如此吗?于是,在没有人介绍、没有人鼓励的情况下,我加入了台湾大学晨光社,正式开始了我的佛学研究。
学佛之初,我还在读一般的佛教书籍,如《无常》!苦!生与死 烦恼 既不排斥,也不动心。一个学期后,上沸下云法师为大专生举办了一次佛法精进讲座。学校有很多人参加,我也去了。那时,我还不知道什么是 "阿弥陀佛",更不用说发愿往生了。我很怕鬼,相信所谓的六道轮回,希望有一个筏子,有一个办法回到生死大海。
皈依之后,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佛教徒了,所以更加认真地研读佛经教义,但对于那些自己还不能理解的教义,我是不会囫囵吞枣、一味附和的。有一次,我向一位前辈抱怨:"什么叫众生皆有佛性?我从身到身,从心内到心外,对自己的佛性一点感觉都没有?" 于是,这位前辈强烈建议我读《楞严经》。
佛陀说:"陛下,您的脸上虽然有皱纹,但您的这一本性却从未有过皱纹;有皱纹的会改变,没有皱纹的却不会改变。变则灭,何苦生死?" 我第一次意识到,佛法不同于世法。世间法着眼于相,随相生灭,而佛法却能从幻相的恒常中看到幻相的无常。
后来在《唯识论》中说,天见玻璃,人见水,鬼见脓血,皆因众生业识不同。啊!业力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,因为心念就是业力的流动,山河大地就是业力的化身。业力无时不在,业力就是一切。一切只是自作自受,自作自受。出家人能转识成智,十方刹土时时清净。于是,我再次发自内心地赞叹佛法,同时也开始忏悔业障,精进修行。于是,我再次皈依谛闲大师,再次参加佛七朝拜,祈求按时证悟 "心无挂碍 "的境界。
大四那年,社团的一位学长举办了一场关于 "中庸之道颂 "的讲座。原本我并不打算参加,但在其他学长的鼓励和督促下,我还是参加了这次讲座。起初,我还有些反应不过来,但当讲到 "然古兰品 "时,我才明白了 "毕竟空 "的含义。火不是一种物质,因为它离不开燃烧的木头,离不开造成 "燃烧 "现象的所有因素。火是因果报应中出现的幻象,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。同样,世间万物都是缘起的假相,没有自性,只有假名。

虚空破碎,大地沉沦,领悟空性之理后,一方面深深感叹佛理的博大精深,另一方面又长叹世间的猥琐与悲凉。如花美眷,终不随大江东去。过去,我总是执着于真、善、美!如今,何为真?什么是善?什么是美?什么是绝对?什么是完美?什么是永恒?人们总想攀登什么,抓住什么。现在,我的手伸出来了,却停留在半空中,无处安放。
我不甘心,却又无可奈何;我想凌空挥剑,却知天地无声,我就像一个失去了力量的病人,陷入了萧瑟的寒冬。这样过了一年,我慢慢明白:"空即无忧,空即解脱,空即自由。既然人生的目的没有终点,那么感悟过程中的诸多变化,不是更有意义吗?冬去春来,大地复苏。
于是,我像一棵树,一方面扎下根来,深入世界本源的虚妄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从千百双手中汲取心泉,万千洪流汇聚成浩瀚的大海。一方面,要登高望远,研究佛教空性学说的真谛。读经研理,静坐观心。"冷眼看世界,风雨从容;回首走人间,逍遥自在"。大局已定!将一生奉献给佛法,是我不可改变的道路和使命。
服兵役期间,我有幸被分配到联合兵工厂的设计室工作。当其他士兵还在为退伍后的前途发愁时,我还在闲读《大般若经》。记得当时办公室的书柜一边是炮弹模型和设计图,一边是佛经,我就夹在两者之间。退伍时,虽然办公室主任和同事再三恳求我留下,但我心意已决,一接到退伍令,就直接到佛光山中国佛学研究部学习。
求学期间,虽然星云法师等长老一再鼓励我,我也曾在普门中学任教,但没过几年,我就因恶业而回乡,留下一个未了的心愿。之后,他去了一家水泥厂工作。在厂里干了一年后,我想,如果我的一生就在几个齿轮、电机和传送带中度过,那将是一种难言的悲哀。如果我想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,拓展自己的人生空间,学佛出家应该是最直接的途径!
于是,我立即辞去工作,住进北投农禅寺,跟随恩师圣谛法师学习禅宗。师父对禅宗有独到的见解,在讲经说法、著述等身,经常谆谆教导弟子如何参禅,参禅到什么程度。尤其重要的是,师父定期组织禅七法会,让我们悟禅与参禅并行,让我们身体力行参禅。
在第二次参禅时,师父让我参 "我是谁",这是我很久以来一直做不到的。由于我对佛经和教义的理解过于自负,在禅七最后一柱香的时候,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:"当一个人没有记忆或睡着的时候,他的心在哪里?顿时,疑云四起,弥漫虚空。此时,困扰我的不再是参禅,而是那句话。参禅两天后,在听经时,我的思绪突然转向 "我不知道我是谁,但我如此烦躁,现在我处于焦虑状态。所有这些焦虑和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?就在那一刻,我的身体和心灵都坠落了,我从所有障碍中解脱了出来。(此文曾以《久久之后,沧海难为水,巫山不是云》为题发表于《菩提树》杂志)。
在这次经历中,我更加深刻地肯定了佛法是世间法,同时也对师父和自己有了更大的信心,出家的愿望也更加坚定。半年后,又一次禅修结束后,由于脉轮不平衡,我的身心并不平静。然而,在一次清洁过程中,当我打开水龙头时,我突然深深地感受到,妄念就像瀑布一样,没有开始,没有结束,也没有恒定和中断。世间万物都是妄念瀑布交织而成的幻影。
此后,每当我坐过一柱好香,坐下来之后再看世间万物,总觉得有一道飘渺凄迷的帘幕横在我与万物之间,阻隔了我与万物,让我郁闷苦闷不能自己,却又不知如何解开。
从那时起,就有了疑惑和阴影----"心是什么?心与物是什么关系?" 它潜伏在我的心里,偶尔出现,先是用黑暗笼罩我,然后又像雾一样消失。一年后,承蒙师父垂怜,我得以外出求学。在高山峡谷中,这个疑虑的阴影依然缠绕着我。
不久,在一次冥想中,我深深地肯定,当下一念本身是清净的,但当分别意识产生,当能量与对象分离,当心与事物分离时,各种欲望、贪婪和嗔怒就会接踵而至,心变得越来越不清净。如果能在万事万物中执着于当下一念,就能获得解脱。然而,这并不容易!
我在古岩寺参学期间,曾问上白西云禅师:"按照《金刚经》的说法,过去心不可得,现在心不可得,未来心不可得,如何才能得宿命神通呢?谢谢他的棍子: "佛法不可说,何必说;佛法不可说,你偏要认为不可说!说罢,他拂袖而去,众人哗然。当晚,我坐禅时,忽然心生一念,顿悟《楞严经》所言:"觉性本明,妄即明觉。万法本来清净,但欲求觉悟却成了无明之根。过去,我总是期望通过思辨、抽象、归纳、演绎来建立思想体系,但现在我意识到这就是无明的根源,不禁哑然失笑,感叹众生的颠倒。
学习回来后,我对如何保养心灵有了更好的把握。我也改善了很多以前轻浮浪漫的习惯。我也进一步体会到了内修大法的意义--做不到的事,反过来做自己。
七月底,师父从美国回来,询问我受戒的事。恰巧在几天前,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: 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徒步旅行,途中却卷入了一场战争,我们不敌对手,情况危急,在退却中,我突然迈开大步,走出了梦境。当我第一次醒来时,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是:"啊!现在我安全了: "啊!现在我安全了,无论敌人如何努力,都无法从梦中出来伤害我。所有的灾难和危险都离我而去了。接下来,我又想到了还在梦中的战友,他们仍然处于危险之中,虽然我非常不忍心,但已经无路可走了!我已经醒了,和他们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。我醒了,他们却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!于是,我决定尽早剃光头,因为我已经醒了,梦境已经与我绝缘!
八月初,在地藏法会的一次禅修中,我感到清净心清晰地呈现在眼前,似乎触手可及。它既不被境界所转,也不被妄念所覆。真与妄是相互独立的。然而,这种感觉很快就模糊了,再也没有恢复过来。
法会结束后不久,又举行了一次禅七,这次的主题是 "什么是无",起初,我无法回应。几天后,我慢慢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妙用:它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底,妄念只能像苍蝇蚊子一样在外面盘旋。谁是天心!我不知道,文字的头颅还能代替它行动吧?
七天禅修的最后一天,早晨我正在修行,门外传来一个声音:"有人在吗?" 我听得清清楚楚,那声音就像一颗子弹射入心脏,引起一连串的回响--有人在吗?有人在吗?谁是我心中的真主?疑云既在升腾,又在弥漫,没过多久,我又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。"有人在说话。"一个声音突然告诉我。然后,每当我听到什么!我就看到了什么!那个声音准确地告诉我看到了什么。"有一尊佛像,有一张佛桌,有......" 本来说的是 "什么都没有",现在却有这么多 "有",真是奇怪!
之后,那个声音一直跟着我。当我听到有人哭泣时,他说:"别哭!" 看到有人摔倒,他说 "好痛!" 渐渐地,我发现这个声音比原来的我更有同情心,更冷静、更公正。每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偏颇时,他都会帮我纠正。"这个守护者七说得太多了!" "他也是好意!" 这两种声音经常互相讨论、协调,决定如何处理外界的刺激。换句话说,我们一直依附的 "我 "现在被分为三个部分:身体的我、意识的我和直觉的我。
下午在花园讲完经后,大师开示道:"禅是无言的,也是无思的。现在回答我的问题,不用你的语言和文字,不用你的经验知识,不用你的思想和分别!"
"你姓什么?" 大师问我。
"我没有姓!" 一个镇定自若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。
"神经病!" 师傅喊道。
"没有!" 不假思索,他又如此肯定地回答。
问完之后,也许是被感动了,他突然泪流满面。师傅拿着香板向我走来。"我不怕!" 声音又高了起来。师傅举起香板要打我!"你不能打我!" 谁回答的?不是我,至少不是我三十年来所认识的那个 "我",但那又是谁?无法形容!难以置信
禅七结束时,在祭祖仪式上,我 "顶礼上师释迦牟尼佛",一想到佛,我又一次失声痛哭。此时,我出家的愿望比以前更加坚定了。参禅结束后,我回家向父母道别,父母非常难过,但也知道他们无能为力。
地藏菩萨圣诞前夕,师父让我们先举行仪式。法会期间,大家的心情都很平静。然而,受戒之后,从法师手中接过袈裟的那一刻,看到旧物的伤感让我泪流满面,那一刻,我确定自己前世是出家人。
佛祖的袈裟,我曾经错怪过它,曾经遗忘过它;然而,生命的蓝图已经烙在我的精神深处,它终将把我引渡到万水千山的彼岸。如今,历经千难万险,我又披上了如来的袈裟。
未来的路会怎样?我不知道,但我确信,我会一步步走下去。
"路虽小,我也要走,担虽重,我也要挑"。
南无释迦牟尼佛
南无智慧文殊菩萨
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
- 迈向自由的真谛,解开978
- 让孩子自由发挥:家长972
- 觉悟之路:佛教修道的957
- 走向佛国的大门:行道951
- 结缘之道:本焕长老谈950
- 校长的演讲在夏令营开949
- 新加坡李显龙总理:揭948
- 轻松阅读的《无量寿经945
- 深入了解心律法师的佛923
- 降伏其心:心性修炼与903